摘要:
神话是超自然或曰超现实的故事,它在口口相传中延续及衍展,对于族群、区域乃至整个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羌”之族名见于甲骨文,其民族历史悠久。羌族保存着丰富的口头文学,践行着古老的民俗传统。他们以“阿巴”相称并奉为先祖的有“阿巴炎”“阿巴禹基”和“阿巴白构”,由此形成的口头叙事、神话意象、符号景观显影在方方面面。羌族通过构建本民族三位“阿巴”的神话意象,既标树我族身份又表达中华民族认同,又在两者融合中呈现族群心性,为今天学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不可忽视。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阿巴”或“阿爸”(国际音标注为apa,下同)是羌语译音,指父亲以上长辈或先祖。“羌”之族名见载于甲骨文,其民族历史悠久。“羌亦东方大族”(吕思勉语),古羌是对驰骋在中国大西北以游牧为主的族群之统称,如今聚居在川西北岷江及涪江上游的30多万羌族是古羌人的后裔,他们以“尔玛”自称,有语言无文字,迄今保存着丰富的口头文学,践行着古老的民俗传统。他们以“阿巴”相称的前辈有“阿巴炎”(apajen)、“阿巴禹基”(apajyti)和“阿巴白构”(apapekou),三者皆奉为“始祖神”。由此形成的神话意象、符号景观显影在史诗、歌谣等口头作品中,也投射在生产、生活等民俗实践中。尔玛人借此意象和符号呈现族群心性,标树我族身份,表达中华民族认同,为今天学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忽视。
一、“史”之神话:阿巴白构是祖先
“羌戈大战”是川西北尔玛人以神话讲述的口头历史,也是他们头脑中至今鲜活的神话意象。以史诗相称的《羌戈大战》本是羌族释比经文中极重要的篇章,如调查者言,“过去凡端公做中下坛法事治病、驱邪、赶鬼、除农害时,均需演唱这部经典。这段故事在茂汶南部、汶川、理县羌区全境广为流传”,其叙事核心是“传说羌族先民从青海、甘肃向东南迁来岷江流域,与戈基人激战后才定居下来”,相关故事亦见于北川等地口碑。“羌戈大战”由主持仪式的释比唱述,其功能有二:一是信仰民俗意义上的祛邪除祟,二是族群维系意义上的讲史叙事。尔玛人口口相传的“羌戈大战”中沉积着他们的历史记忆,传递着族群心声。
黄河、长江是孕育中华文化的两大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史称“西戎牧羊人”的羌是“以养羊为特色的民族”,原本驰骋在西北广大区域的他们又在东进南迁中书写历史,把诸多故事铭刻在滔滔江河流域。古羌在中华民族演进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在长时段族际交往中有的东进中原融入华夏族群,大多数沿着横断山脉六江流域自北向南迁徙,与其他族群发生交往、交流、交融(费孝通先生因此称羌是“输血的民族”),其中一支来到岷江上游区域,繁衍生息至今。从口头文学切入羌族历史,就会发现因“战争”而“迁徙”这类主题为他们世代不忘,投射在神话传说、民间艺术以及仪式行为中。《羌族词典》收录释比经文《羌戈大战》并云此乃“羌族史诗”,该史诗讲述了尔玛人的祖先“历尽艰难困苦,与戈基人战,与魔兵战,从西北迁居岷江上游地区的历史真实”。羌族口头文学中关于戈人的叙事不少,据考古发掘发现,戈人墓葬“自汶川县沿岷江上至茂县,西至理番,为数至多”,这正是羌人自松潘沿岷江南迁的路线,即今天羌族聚居的主要区域。“羌戈大战”所述羌、戈之间战争的时间大致在秦汉之际,也就是古羌人从西北黄河上游经松潘草地向南迁入岷江流域期间。该长诗通过叙唱古羌历史塑造了迁徙群体首领阿巴白构的艺术形象,他是定居在岷江上游的尔玛人奉为先祖的民族英雄。目前《羌族释比经典》搜集整理的该史诗含十个章节,分别为序源、释比诵唱羊皮鼓、天降白石变雪山、羌戈相遇日补坝、长子四处查神牛、木比授计羌胜戈、竞赛场上羌赢戈、木比施法戈人亡、羌人格溜建家园等。史诗开篇即“唱起古歌敬天神,唱起古歌颂祖先”,唱述“他们从旷野的戈壁滩迁徙而来,他们从莽莽的草原上迁徙而来”。
“羌从哪里来”,2008年汶川地震后推出的大型歌舞《羌风》中有此设问;“想当年,居河湟,创业几多艰”,羌族神话剧《木姐珠剪纸救百兽》中有这叙史。河指黄河,湟是黄河上游最大支流,“河湟”指二者间的广阔地带。林向认为,“西北羌族的形成,约在战国之世。……战国之世,中原羌族残部西逃,与当地原始氐族融合,才形成‘河湟之间’的西羌诸族”。河湟流域的人类史前文明亦丰富,如1980年在青海贵南发现的拉乙亥遗址,便是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阶段的文化遗存,有灶坑、烧土、石锤、砍砸器、刮削器、研磨器、雕刻器、骨锥、骨针等诸多呈现上古人类生活之物,该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川西北羌族以河湟为祖居地的言说见于神话传说。《羌戈大战》透出古羌的“真实经历”,包含着其从“河湟”到“江源”的迁徙历史和族群记忆。学界指出,“羌族之先祖,早期居于甘肃辛店、李洼一带”,而“羌人早从新石器时代即由西北向南迁徙”。在羌族口头文学中,“羌戈大战”既见于韵文表达也见于散体叙事,其中对羌人自河湟南迁的征战经历有着力渲染:一是与魔兵大战,导致羌人九部被迫分散迁徙。通过锡拉的神助,阿巴白构施法将白石变雪山挡住了追击的魔兵;二是部落到达岷山日补坝后与戈基人交战,在天神帮助下最终战胜了戈基人。关于古羌人迁徙的神话叙事,亦因各讲述者而有异同,形成了多样化文本。对于这个迁徙故事,法国学者石泰安写道:“由于他们被迫进行迁徙,经过一年多的流浪之后最终落脚在他们现在的住处。在达到那里时,他们又必须同当地的一个叫作葛族的原始民族进行斗争。这后一个民族的人可能非常强大,但愚昧无知。……一位天神向羌人指出了战胜葛人的方法:应该用木棒和石头袭击他们。”。在天神指点下,阿巴白构率领羌人进入四川来到岷江上游,首先落脚在“热兹”(松潘),继而到了“格溜”“日补坝”(茂汶)。来到新的居住地后,羌人“建村筑寨扎营盘”,大兴土木砌碉房修堡寨,“阿巴白构住寨内,日夜操劳百事管;分派九子住九寨,十八大将镇四边”。历经“战争和迁徙”的羌人终于安定下来,在“岷江河畔建家园”。为了管理好羌地,首领阿巴白构将九个儿子派驻各方,如长子与父亲在格溜,幺儿巨国基在巨达。从此,这片区域逐渐发展为羌族聚居地。
对于迁居川西北的尔玛人,阿巴白构是他们来此谋求“立地根源”的开辟先祖。在山高谷深的岷江上游,这口头历史在羌族村寨中代代相传,除了释比经文和民间故事,还折射在尔玛人的美术遗产和民俗实践中。如美术考古方面,在茂县、汶川、理县出土的彩陶从形制到图纹皆跟陇西、陇南的马家窑彩陶类型相似,彼此有明显的亲缘关系。追根溯源,“黄河上游彩陶向长江流域的南传,是由甘肃南部经嘉陵江上游到达岷江上游地区”,在川西北羌地出土的彩陶基本可划归马家窑类型。又如在茂县北部渭门、沟口等乡,人死后葬礼上有北去草地买马的仪式,该习俗关联着古羌迁徙的历史记忆。传统使然,象征性“赶马”仪式是丧礼中不可少的环节之一,在灵堂由释比主持施行,“相传渭门沟羌人的祖先是从松潘草地经较场、叠溪来到渭门沟,此地羌人死后要到松潘草地买马,让死者亡灵骑马到西天”,还要“用羌话歌唱到松潘草地买三匹马,一匹亡人骑,一匹家人用,一匹送舅家”,从亡灵追思到生者现实,仪式无不意在强化族群迁徙的历史记忆。在明代徐霞客确认长江源于金沙江之前,岷江长期被国人视为“江源”(长江源头),其在中华文化史上地位甚高。上述九子掌管之地,根据自北而南流淌的岷江这条中轴线,以阿巴白构驻扎的“格溜”(茂县)为中心,东去“巨达”是北川,南边“罗和”是灌县,西去“波洗”是理县薛城,北边“热兹”是松潘,其他如“夸渣”在汶川,“兹巴”是黑水等。撩开神话的面纱,“羌戈大战”中这番翔实的地名记录和空间勾画,大致与今人熟悉的川西北羌族聚居区(汶、理、茂、北)相吻合。又,神话《羌族自古立地根源》亦属“羌戈大战”故事系列,是1980年从88岁释比袁世琨口头采录的,其中羌人首领“构”即阿巴白构。在此叙事中,阿巴白构具有神性血缘,他是天女木姐珠与斗安珠夫妇所生九个儿子中的老大,与魔兵和戈人作战的“九子也封为人皇”。
民国初期来岷江上游的英国传教士陶然士(Thomas Torrance)曾用异邦宗教解释羌人的民间信仰等,试图证明羌之族源“西来说”,此解释带有西方殖民话语色彩。第一,上述以英雄先祖“阿巴白构”为叙事焦点的羌族神话传说正提供了和陶然士相左的反证。对此,头脑清醒的国外研究者亦有反思:大而言之,拉铁摩尔就指出在追溯中国文化源头时,“西方学者则被他们所相信的中国文化大半是由中亚‘输入’‘移植’及‘文化传播’的偏见所影响”;小而言之,亲身赴羌寨做田野调查的美国学者葛维汉也不无“自信地说在史料或中国历史上中还没有发现或听到资料证实川西羌人的祖先来源于西亚,或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后裔的说法”。葛维汉又说:“相反,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羌人居住在中国的东南部,他们向西迁移,有些进入了甘肃,另一些又往南到了川西和川南。”第二,从文学人类学透视川西北羌族关于祖居河湟与迁居江源的神话历史言说,不难看出其自觉归属中华本土民族大家庭的文学表白。第三,着眼中华版图,岷江古称“江源”而“河湟”地属黄河,从古到今,尔玛人以其历史和现实沟通着黄河、长江,在中华文明这两大母亲河之间演绎出种种风云故事,从而为我们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一个有特色的个案。
二、“龙”之意象:阿巴禹基生西羌
“禹主治水。”大禹是上古治水英雄,是撩开华夏文明史帷幕的夏之基业的开创者,是中华多民族敬奉的英雄祖先。“禹是辟地大神”,丁山有此断语并在跨文化视野中解析人类史前洪水神话时指出:
自有人类到现代,人类的文化,经过了种种折磨,受过了种种灾难,一波三折地向前进展:最严重的灾难,要推洪积纪的那几个冰期……“新冰期”之后,全世界受冰雪融解的洪水灾难,予人类以不可磨灭的回念。公元前廿三世纪巴比伦人最古的文献记录巴比伦历朝兴亡表,是追叙“大洪水”为有史记事之始。
印度古代的摩奴法典以至美洲印第安民间的传说,一提到人类历史的开端,无不从“洪水”说起。这样看来,尚书以尧典开篇,显与摩奴法典创世纪意义相同,也是说中国有史时代自“汤汤洪水方割”发轫。禹平水土,当然是中国的“辟地”大神;所以两周王朝与列国的重要文献,一回溯远祖的历史,必断自伯禹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诸子创教篇说,“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故大地民众,皆区萌于夏禹之时”,是相当正确的观察。
笔者查阅资料可知“禹兴于西羌”“大禹出西羌”“大禹出于西羌”这些见于古籍的材料,在今天羌族地区所编的有关大禹的书籍中屡见辑录和引述;在川西北羌族地区,大禹传说见于汶川、北川、理县和茂县,他也是尔玛人心中的治水英雄和神圣先祖。据调查,释比经文中有《竽巴热色》,即是“敬颂大禹神”的篇章;后来出版的《羌族释比经典》也收入《颂神禹》。按照巴蜀民间表述,生于西羌长于江源的大禹王不但治理了西部岷江水患,后来还“被中原盟主请去制服黄河去了”,从此在兢兢业业“平水土”中完成了“分九州”为华夏奠基的大业。由此,“春秋以前,自王朝至于列国的一般重要文献,每一追溯中国历史的起点,必以禹为嚆矢”。大禹之“大”,在汉语是“后人对禹之尊称”;羌民称之为“禹基”(jyti)并在其名字前冠以“阿巴”(apa),尊称“阿巴禹基”(apajyti)。大禹是人也是神,在尔玛民间口碑中,神王大禹生下来三天能说话,三月会走路,三岁就长成臂如红松、身似大山般强壮的汉子。相传在汶山郡大禹出生地,“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逃罪者来此地而“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究其缘由,盖在“大禹之神所祐也”。泱泱中华,炎黄子孙自称“龙的传人”,尔玛人不但将英雄崇拜与先祖敬奉重合,且进而将其心目中的阿巴禹基具象化为“龙”的神话意象,由此演绎出富有地域和族群特色的口头篇章。
岷江上游的旅游景区九寨沟和黄龙均在松潘。《暗海鱼》是1987年3月从镇坪乡王姓羌民口头搜集的,故事有关松潘黄龙寺。该寺山下有个暗海子,每年五月会有许多头带红点的鱼儿涌出。此鱼来历不凡,相传大禹疏通九河时,虽收拾了天上的妖怪,但还有水下九妖十八怪未降服。大禹请来寺中修道的黄龙,后者入江打败了妖怪。治水大业完成后,黄龙婉拒大禹王请其做官的邀请,回寺里仍过他的仙人生活。因黄龙爱吃鱼,禹王便将南海切下一角移到黄龙寺山下作为暗海,里面养鱼,以示酬谢。岷江发源于松潘弓杠岭,神话另有版本讲“大禹治水的决心感动了住在弓杠岭下的一条黄龙”,后者“帮大禹查清了水路”。大禹奏请天王木比塔赐封黄龙为神,但黄龙不愿受封,人们便“在松潘修黄龙寺纪念它”。按照神话叙事逻辑,黄龙之所以听命于禹并助禹治水,盖在阿巴禹基本是奉天命下凡的“龙神”,是“龙神投胎石纽地”,而“在羌人的心目中,龙神的地位仅次于天神和地神”。视大禹为龙神在羌民的口头表述,又见于1986年4月在北川县禹里乡搜集的《端阳节的来历》,故事明言“禹王是龙神,他开山造河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老龙都喊起去”,诸龙皆听从禹王调遣。以上羌族神话不免使人想起汉文古籍所载:“昔禹南济江,黄龙夹舟,舟人五色无主。禹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养民。生,性也;死,命也。何忧龙哉?’于是二龙弭鳞掉尾而去焉。”这个故事也载于《吕氏春秋》。鉴于阿巴禹基的“龙神”(可谓“龙神之王”)身份,水中黄龙在“受命于天”的禹王指点下也服服帖帖。在汉文古代文献中,江河里鱼龙之类神物辅助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先秦诸子笔下屡见记载,如“禹理洪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处,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中”。今在湖北武汉,汉阳江滩公园有大禹治水雕塑群,其中《河伯献图》便据此题材创作。此人面鱼身的河精或河伯即河神,是司水之神,他前来献图助大禹治水。古有“应龙”助禹治水神话,袁珂释《楚辞·天问》“应龙何画”引王逸注“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时,指出“应龙”即是“黄龙”。该神话传播广泛,《太平广记》卷二二六“水饰图经”条载:“禹治水,应龙以尾画地,导决水之所出”。《拾遗记》卷一亦云:“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与后。”袁珂认为这涉及两种治水方法,“‘黄龙曳尾’,是为疏;‘玄龟负泥’则为堙。……是禹仍堙疏并举”。在巴蜀地区,据考证“宋代以前三峡一带已有黄龙助禹治水的传说”,但尔玛人的叙事很“在地化”,带有羌文化特色。民国《松潘县志》之“黄龙寺考”中对此故事有引述,当地民间口碑亦言“夏禹治水到茂州,黄龙为其负舟导江”。中华大地上流传的种种神话与川西北羌族关于阿巴禹基是“龙神”的故事息息相通,从中可窥其原型默契。
对于川西北尔玛人而言,阿巴禹基是为他们救难解忧的英雄先祖。在羌民信念中,来自西羌长于江源的阿巴禹基之所以有理水、治水之神功,能为天下生民除水患保平安,盖因他是“龙神”下凡转世。龙神崇拜见于羌族民俗,释比经文唱述天神木比塔的三儿司赤波是掌管雨海江河的龙神,族群古称“冉駹”在羌地文人看来也应是“取龙马相合之意”。文化发生往往离不开自然环境,川西北羌族敬奉治水英雄大禹跟他们生活在高山深谷而面对地质灾害频发的严峻处境有关。中国大陆地貌呈三级阶梯式,西高东低,四川处在从最高到次低的交接部,崇山峻岭中江河切割,地貌复杂。在青藏高原东南缘羌族聚居的岷江上游,大部分区域位于新华夏系“龙门山式”断褶构造体系,新构造运动格外强烈。这里山高谷深,地震、洪水、泥石流等频频发生,从松潘到汶川的一系列堰塞湖都与地震有关。典型者如叠溪堰塞湖、茂县文镇堰塞湖、古尔沟堰塞湖等。对此灾害,汉文古籍从《汉书》到《华阳国志》等屡载,百姓口头亦故事多多。每年夏日雨季来临,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也须时加提防。因此,尔玛人敬奉阿巴禹基,寄希望于“龙神”治水也就自然。从族群心理看,川西北羌族奉大禹为先祖,亦跟其身为边地族群的历史性焦虑有关。本居西北之羌作为与中原腹心相对的“蛮夷”,其族群地位向来被强势话语指认为“非主流”“非正统”,甚至成为王朝“征伐”“平定”对象(如“殷代羌与商为敌国,卜辞中多有伐羌、逐羌、获羌等记载,且每用羌为人牲,以供祭祀”)。汶川绵虒有刳儿坪,相传是阿巴禹基降生地。民国时期学者卫聚贤来此调查禹的传说,与年老羌民对话时后者说:“汉人不应当叫我们叫蛮子,大禹王也是羌人,是不应叫大禹王蛮子的。”如此焦虑,渗透民间。史学家顾颉刚梳理先秦民神杂糅历史时指出,“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这是使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这是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历史上,“平水土,分九州”的禹为夏之奠基者,代表华夏正宗。尽管“羌和华夏发生关系,不知始于何时”,但在顾颉刚看来,“羌、周两大朝均由西方勃兴,羌对华夏的历史关系一定非常深切”。地处西部山地平原交界,视大禹为“先祖”,尔玛人构建大禹神话用心良苦。禹、羌关系之历史真相如何可继续探讨,但无论从自视为夏之后裔还是从怀有“归往”之心看,羌对禹的认同是实心实意的。这种认同的深意还在于尔玛人要借此洗刷外来的污名化指认,宣示“我族”作为华夏“国族”成员的合法身份。
与四川相连的陕西汉中如略阳、宁强(宁羌)是古羌栖居之地,在此区域夏代有褒国,乃禹之子受封之地,《国语·郑语》等书载有夏末褒国君主神化为龙之传说。作为神话思维的符号化产物,“神龙”意象从禹夏到禹羌其来有自。川西北尔玛人运用原始思维以龙神意象附会于大禹传说并不奇怪,从某种程度上不妨说是他们在以婉转话语加入自视为“龙的传人”的中华民族大合唱中。无论“夏”的后裔还是“龙”的传人,无论族群心理表白还是神话意象构建,尔玛人通过口头表达、行为实践和符号编码都在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看齐。
标题一
“中国古羌城”位于岷江西岸,与茂县县城隔江相望,是2008年大地震后川西北羌族地区新建的文化地标。该羌城地处“金龟”和“银龟”两个山包之间宽阔地带,目前是通过文化再生产集中展示羌族文化的最大平台。两座山包,居北者有祭祀天神的高高的木比神塔,居南者有石砌碉楼式的祭祖大殿。后者包括三殿,除了大禹殿和元昊殿,便是主祀炎帝之殿。殿内,阿巴炎金色巨像居中端坐,头有双角的他手握麦穗,神态庄严。门前,有石碑刻着介绍文字:
炎帝,号神农氏,中国羌炎(姜炎)农业文化创始人,开创农耕,造福人类,被民间敬奉为神农大帝,系第一代羌族先贤先圣,中华民族开山始祖。公元前3796年,其出生于今陕西省渭水流域。史载:炎帝姜姓氏族由善于治水的共工四岳羌人起源,逐步沿渭水黄河流域向东发展至今河南、河北、湖北、山东一带中原地区,由畜牧业逐渐向农耕转移,“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
羌城内又有景点“先龙坪”,介绍云:
先龙坪为羌人大型祭祖场所,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在羌山大地广为流传。为缅怀炎帝神农氏开创畜牧业、农业、羌医药的丰功伟绩,羌人每年都要在此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同时建石塔纪念历代羌王羌圣,以晾晒形态展示原始农耕文化、羌医药文化成果。羌族是感恩的民族,先龙坪的文化内涵,就是羌族敬天法地、不忘祖宗、知恩图报、忠孝仁义的文化展示载体。
茂县城南有个在羌族聚居区颇有知名度的避暑山庄,其中有羌圣祠,该山庄由民营企业资助修建,落成时间为“2002年11月5日壬午十月初一日”,即羌年期间。那是“5·12”地震前尔玛民间自发建立的祭祖场所,塑有以炎帝为首的雕像群,介绍云:
炎帝,姜姓,羌族。生于公元前3976年,出生在陕西省宝鸡市姜城堡。《史记·帝王世纪》载,炎帝“始教天下种谷,故号神农氏”,中国姜炎农业文化始祖。
这些文字出自当代羌族文化人士之手,突出了奉祀炎帝为尔玛人的先祖这一主题,有两点可引起关注:一是姓氏上的羌姜认同,二是生产上的农耕文化。
羌、姜认同是典范化羌符号构建的重要体现。甲骨文有“姜”,构形为从羊从女,与《说文》“姜”之篆文略同。古汉语中“羌”“姜”相通,“作为姓氏的‘姜’和作部族名的‘羌’二字,在中国古音上是一致的”,而“‘姜’应是羌人中最早转向农业生产的一支”。姜、羌相通,“羌转化为族名,姜则成为姓氏”。《说文》云:“姜,神农居姜水以为姓,从女、羊声。”历史上,“炎帝族应是最早从事农业的民族之一,所以后人才称之为‘神农氏’”。开创农业的炎帝随母族姓姜,辅周的姜子牙也是此姓。“姜子牙,名姜尚、吕尚,尊号姜太公,生于山东齐国,炎帝四岳后裔,羌族杰出的军事家、思想家。……文王姬昌尊姜子牙为师,共谋兴周灭商大计。”茂县中国羌城炎帝殿内配祀姜子牙像,有此介绍。羌城侧坪头羌寨有经灾后重建修葺一新的“羌祖庙”,且看笔者2012年的走访记录:
该庙不大,据说始建于清道光年间,“5·12”地震时受损。修葺后的庙子,系歇山式二重殿,青瓦盖顶,飞檐翘角,墙体为赭红色,建筑样式跟村里平顶式民居形成对比。……下午上山去,笔者看见前殿门上挂着崭新的金字横匾是“羌祖庙”,并配以印章式“祖德流芳”四小字,匾上挂红。门锁着,无人看守,也不见有其他游客。透过门窗玻璃望去,有三尊金身人物立像,正中是手握稻穗的炎帝,右边是手中执锸的大禹,左边是手握书册的姜尚。历史上,开创农业的炎帝,辛劳治水的大禹,都被今天的尔玛人视为先祖,称之为“阿爸炎”(apajen)、“阿爸禹基”(apajyti)。……辅佐周武王打天下而在民间传说中发榜封神的姜子牙,也被羌人视为神灵,在家中供奉其牌位。
尔玛人祀姜子牙非今天才有,据20世纪80年代理县桃坪释比杨步山口述,释比经文中有上坛经《南安且》,是尔玛人还天愿祭姜子牙所唱,并以一只红公鸡献祭。20世纪上半叶,赴岷江上游调查的葛维汉在记录中写到,尔玛人“认为汉族的神灵是真神”并崇拜之,释比辟邪咒语中也有“姜太公到此”。石敢当崇拜在川西北羌区亦流行,且与姜太公信仰重合,如在理县桃坪乡增头羌寨,人家将其供于中门左侧,即进门右边,礼拜有加。
农耕与血缘是古代中国社会得以建构的两大基石,相关理念作为“集体无意识”渗透在方方面面。夏商周三代开启了华夏史大门,“周民族是有史可考的最早农业民族”。追溯历史,“周以羌人为其始祖母”或“周武王的祖母是一位羌女”,盖因周人的先祖弃(后稷)是其母姜嫄感神迹而生,事见《诗·大雅·生民》等。“这个姜姓的羌,乃周室姬姓的姻亲部落,却是一个农业高度发达的部落。”羌、周之密切关系,除了族际通婚,亦见于来自西部的羌人“前歌后舞”助周伐纣(2008年“5·12”地震后笔者走访茂县坪头村看见有石刻展示“羌族军傩灭纣”画面,去陕西宁强羌博园亦见有同类展示)。历史上,殷纣属于乱世昏君,周伐纣代表替天行道,羌助周则意味着对华夏王朝正统的认同,这是不含糊的。“角角神”是川西北羌族所奉神灵,当地民间有《角角神的故事》,采录于20世纪80年代,故事云:“在远古时代,汶山郡(现在的汶川县)的一个山寨上,有个叫羌源的妇女,她是炎帝的后代。”羌源的儿子羌流也是母亲感神迹所生,整个故事跟《诗经》记载的周朝始祖弃(后稷,其母姜嫄)故事很接近,故《茂汶羌族自治县概况》云“周的祖先弃是羌人姜嫄的儿子”。这个羌族民间故事又题作《尕尕神》,列入“神和神性英雄神话”,采录于汶川县草坡乡,其中羌源作“姜原”,羌流作“姜流”,故事开篇云:“古时候有个神女,名叫姜原,她是阿巴白叶的女儿……”关于羌族神话中姜原感神迹生子故事,笔者结合古史传说另有专文论述和辨析,兹不赘言。阿巴白叶又写作阿巴白耶,他也是尔玛人所奉先祖。释比经文诵唱其事迹,说他降生在天地未分时,能力比天大,他和妻子去龙池求子,“神灵感应得了孕”,有了三个儿子,学艺后大儿子“成了端公木匠师”,二儿子“成了羌家狩猎神”,三儿子“耕种务农成祖师”。准此神话,阿巴白耶的三子分别成为释比祖师、狩猎之神、农业祖师,这种信仰正对应着羌族生产生活的三个重要方面:信仰、狩猎、农耕。历史上,祖居大西北的羌人本以牧猎为主,迁居川西北的他们则以农耕为主,羌人这种生产生活的变化便投射在《羌戈大战》中。
对于川西北尔玛人而言,阿巴炎是标示他们生产生活现状的农耕先祖。《羌戈大战》之名是搜集整理者定的,这部释比经文原本叫“毕格溜”(羌语译音),意为“吆猪经”。为何“吆猪”?去哪里“吆猪”?是从川西坝子吆猪到岷江上游饲养,归根结底,这标志着来江源定居的尔玛人从牧猎到农耕之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转换,大西北以牧猎为主的羌人从此成为川西北以农耕为主的羌人。养猪是农耕生活的重要标志,“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凡已出现原始农业的地方,都有养猪的遗迹出现,反之亦然,说明了养猪与农业,一开始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养猪至今在川西北羌族聚居区仍是重要的副业,猪膘肉乃是尔玛人待客的席上美味。透视神话意象,了解上述史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尔玛人为何高度认同开创农业的炎帝。当然,在以“炎黄子孙”自豪的中华民族语境中,认祖归宗的他们也在讲述自己身为“炎黄子孙”的古老故事,表达出对中华大家庭的认同。通过神话叙事,川西北尔玛人就羌、姜关系追根究源,他们对阿巴炎及相关历史名人的敬奉更加自觉。这种基于农耕中国的“姓”之认同,在诉诸观念上“想象的共同体”的同时亦透露出某种血缘攸关的根基性族群认同。
四、结语
“神话是什么?为何它具有如此强大的魅力?”音译“迷思”(myth)的神话是超自然或曰超现实的故事,它在口口相传中延续及衍展,对于族群、区域乃至整个民族共同体具有不可小视的整合力。“世俗”与“神圣”构成人类生活之两面,对于身在俗界的人类来说,幸好有精神层面的“神圣”指引其摆脱杂乱无序,“为人们提供了救援与幸福”,神话作为神圣的象征便意义在此。宗教学家斯特伦在论述“借助神圣的象征创造共同体”时指出,神话“以象征的创造力把人的存在秩序化,并成为一个意义的世界”,而“对于生活于其规范作用中的人们来说,它具有终极的价值”;口头神话及其仪式实践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们创造了共同体,并给予人们力量,使人摆脱持久而又徐缓的变化”,维系着族群存在和发展。斯特伦谈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时说:“在他看来,无论什么宗教与神话,对于置身其中的人们来说,都是有价值的、充满意义的。”又说:“结构主义者不是把古代民族与当代民族中流传的神话、传说与故事当作毫无意义的迷信谎言;相反,他们认为这些表现形式以其严密的逻辑作用于意义的交流。”着眼古代,立足当代,从人类学族群认同角度研究羌族先祖敬奉的“神话历史”(mythistory),无论从神话看历史还是从历史看神话,当从“表现形式”之表层穿透到“意义交流”之深层,从而实现对其文学、艺术乃至心理、行为的应有把握。王明珂结合神话与历史析说西方阐释学者保罗·利柯的“历史性”概念时指出,“利柯以‘历史性’简洁而有力地说明叙事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人们书写历史,并生活在为历史形塑的社会现实之中”。换言之,“人们书写‘历史’,沉浸在‘历史’所规划的社会现实中,个人因此也是‘历史’的生成物。就是说,一个人的某沟、某寨人认同,以及在此认同下其应有的社会行为,皆受到他相信的‘历史’的塑造”。因此,“‘历史’是本土观点所见与‘现在’密切相关的‘过去’”。归根结底,“神话历史更加强调历史的文化认同性,而不是对于史料的客观分析之科学与事实”,其“最基本的核心在于文化阐释”。因此,基于本地认知,关乎地方取向,折射往日故事,表露当下意愿,彰显身份认同,这是我们研究羌族有关三位“阿巴”(先祖)之神话历史的口头讲述及符号表达时不可忽视的。通过这种讲述和表达,尔玛人将“我族”历史呈现又被此历史形塑,从而亮明自我身份,传递族群认同,也沟通族际关系。着眼大局从“核心价值观”看中华认同,川西北尔玛人通过构建本民族三位“阿巴”的神话意象既表达了族群心声也整合了族群意识,他们“借助神圣的象征”为“创造共同体”所作的全部努力在于:一是身为尔玛人内部的我族认同,一是身为大家庭成员的中华民族认同,这两种认同又有机融合,表里相依地构成其族群表述整体。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转自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声明:本公众号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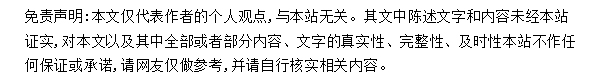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